職場 | 教育趨勢
「請來點更高段的競爭力吧!」大人們,請不要把自己的無知投射到寒暑假作業上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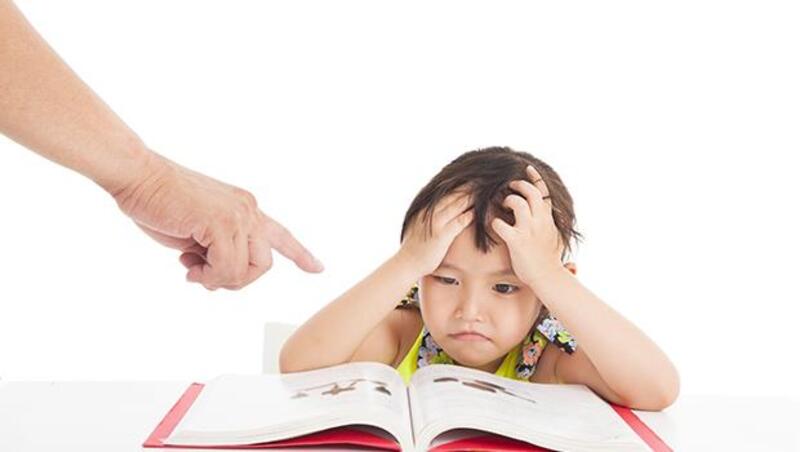
台北市教育局在寒假前夕,率先廢除了國小強制性的寒暑假作業,改由學生自主決定作業內容,並在開學之後報告。這個形式頗類似日本學生寒暑假的「自由研究」,在教育理念上是一大進步。也如同所有進步的教育舉措一般,引來不少家長和教育工作者的批評。
目前的批評主要有兩個方向:
1.取消寒暑假作業,會讓學生少了3個月精進學業的時間。
2.讓學生自行決定作業內容然後報告,會突顯學生間的貧富差距。
但是,這兩個方向都是站不住腳的。這些批評反應的並不是這個政策的問題,而是這些大人們自己的無知與保守。
寒暑假作業才不會精進學業
第一點是苗栗縣斗煥國小校長陳招池提出的。她的〈取消寒假作業國小校長:柯P割錯盲腸〉一文當中,有一大堆不符教育學實況的錯誤預設,凸顯的正是部分不思長進的教育工作者的無能。首先,她預設了學生沒有任何自主學習動機,必須靠強制力推動,但事實上,教師最重要的任務就激發學習動機。如果你無法激發學生的動機,怎麼教效果都很有限,坐在教室再久、作業寫再多,你也管不了他放空的腦袋。陳招池的說法是推卸責任,把教育工作者該做而做不到的無能,轉嫁給學生。
其次,他預設了「寒暑假作業可以精進學業」,這個想法也是錯誤的。在台灣,「學業」的內容基本上大部份都是記憶性的知識,少有實作性的技能。我們就算不去挑戰這些知識是否有價值,在漫長的寒暑假中,光是分配作業是不可能達到知識的精進的。
在學習一項知識的時候,有兩個重點:一是「少量多餐」,二是「立即修正」。所以如果你要精熟100題數學,分成10天各寫10題,會比分成兩天各寫50題效果好;而且如果你寫錯了,最好在當下立刻得到回饋,馬上修正,不然時過境遷,你會忘記自己的思路錯在哪裡,就算告訴你答案也沒有用。
由於學習的這兩項特性,本質上就註定寒暑假作業不可能有任何用處。一來時間拉得太長,除非學生真的乖乖每天寫一點作業,否則「複習」也不會有什麼效果;二來沒有教師在身邊指導,不可能立即修正,至少要等好幾個星期。
前者跟陳校長的前一個預設完全矛盾—不是說學生沒有自主學習動機嗎?你要如何確定他會每天寫一點,而不是擠在第一週或最後一週?後者更是可以從實務上得到驗證,有多少老師會認真批改寒暑假作業,然後詳細檢討的?這並不是老師們打混,而是與其做這麼沒效率的事,不如把時間先拿來複習或教授新進度。
是凸顯孩子的貧富差距,還是大人的階級歧視?
而說到自由發表作業內容,會凸顯貧富落差,這更是家長們自身階級歧視和駝鳥心態的投射。首先,社會生活的實況本來就是有貧有富,不從學校的團體生活裡,開始讓學生練習不因家境自卑、也不因家境自傲—這基本上是同一件事——能平等善待不同處境的人的態度,我們如何期待他們畢業之後能夠有現代公民的基本教養?
把不同特性的學生同質化、抹平,並不能讓學生學會「平等」,因為他們根本沒機會練習面對「差異」。
其次,「讓學生自由報告會凸顯貧富差距」這想法,本身就是階級歧視的產物。有些人認為,如果同一班學生,有人發表出國玩的照片、有人卻只能幫忙家裡擺攤,那怎麼辦?不用怎麼辦。會覺得這樣有問題的人,本身就是階級歧視,認為出國玩的經驗會比擺攤的經驗有價值。這正是我們在談教育的「多元價值」時要對抗的。如果學生分享如何炸雞排才能更酥、怎麼樣才能一次記住20個客人的點單,或者照顧臥床的爺爺奶奶有什麼注意事項,這難道不是比學生飛去其他國家泛泛遊玩更有價值嗎?
更重要的是,透過這樣彼此分享,學生才更有機會看見不同的生活樣貌,跨出自身經驗的侷限。現代公民要學會的是面對「差異」,而不是把差異隱藏起來—這種隱藏,反而正是在對學生釋放「你的生活是可恥的、不能拿上檯面的」這類負面訊號,這才真的會複製階級歧視。
來點更高段的競爭力吧
最後我要回應一種廣泛出現在各種教育議題,反對進步的教育改革的說法:有些人認為,讓學生「自由」,可能會減損學生的「競爭力」。
這個說法是錯的。
檢測方式很簡單,你只要觀察現在40歲以上的台灣人,跟全世界40歲以上的其他國家國民,到底哪國人比較有「競爭力」,你就會知道,越自由的教育環境,會帶來越強的「競爭力」。
因為在這個世界上,真正高段的能力,是面對差異的能力(如上面所說),是說服的能力(如何把自己的寒暑假生活講得很厲害?),是發想的能力(在暑假做什麼事會有梗,可以在開學時逗笑我喜歡的人?),是後設思考能力(如何把電動打得更強,寫成一份攻略?),是規劃複雜專案的能力(如何設計出一個讓全家人驚喜的父親節?),是動手實作的能力(我想cosplay「進擊的巨人」,怎麼弄出那一身皮膚?),是人際溝通的能力(我能成功邀請5個朋友跟我去爬山嗎?),是整合資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(我想要組模型,要做到什麼事情,才能存到錢or讓爸媽答應我買?)⋯
這些通通都是「競爭力」。
平常在學校課程的進度下,學生不可能有機會去練習的。每年有3個月時間,分出來讓他們嘗試一下,有何不可?
既然要談「競爭力」,就從小讓學生學最好的,何必浪費時間,去反覆琢磨那些長大成人之後,大部份都沒有實用性的知識?你有聽過誰因為很會背九九乘法表、或者很會寫測驗卷而成為一流人才的嗎?
來點真正高段的競爭力吧。
 專欄簡介_戰神系作家時事導讀
專欄簡介_戰神系作家時事導讀
朱宥勳,1988年生,清大台灣文學所碩士。現專職寫作。
從小就是乖學生,並且以教師辦公室為遊樂場。待過私立學校也待過明星學校,擔任教育工作者時,站過學生成績PR值99到PR值沒有底限的各種學校講台。從一個好學生,變成一個越來越不信任台灣教育體系的教育工作者。
我們總是說教育能夠使階級流動,但實際上是鞏固階級。能夠站上講台、搖筆為文的我們,都是穿過這張殘酷篩網的倖存者。
台灣的教育體制,本身就是參與一套血淚斑斑的共犯結構。我們傷害過的、排除掉的、無能為力的每一個學生,都是蹉跎他人好幾年生命、甚至一輩子的一支大過。教育提供的希望和機會是必要的,但卻只分給那麼一點點人。能不能再把網格撐大一些?
改革總是來得太慢,寫在這個專欄裡的諍言,是我做為一名教育工作者,一筆一畫寫落的銷過日記。提醒自己永遠記得那些來不及挽救的、正在發生的、將要毀壞的⋯⋯然後試著多守住一些尚未來到的。
商周大調查

川普關稅恐慌擊潰股市,投資怎麼辦?專家:不該改變你的整體計畫!

朱宥勳,1988年生,清大台灣文學所碩士。現專職寫作。
從小就是乖學生,並且以教師辦公室為遊樂場。待過私立學校也待過明星學校,擔任教育工作者時,站過學生成績PR值99到PR值沒有底限的各種學校講台。從一個好學生,變成一個越來越不信任台灣教育體系的教育工作者。
我們總是說教育能夠使階級流動,但實際上是鞏固階級。能夠站上講台、搖筆為文的我們,都是穿過這張殘酷篩網的倖存者。
台灣的教育體制,本身就是參與一套血淚斑斑的共犯結構。我們傷害過的、排除掉的、無能為力的每一個學生,都是蹉跎他人好幾年生命、甚至一輩子的一支大過。教育提供的希望和機會是必要的,但卻只分給那麼一點點人。能不能再把網格撐大一些?
改革總是來得太慢,寫在這個專欄裡的諍言,是我做為一名教育工作者,一筆一畫寫落的銷過日記。提醒自己永遠記得那些來不及挽救的、正在發生的、將要毀壞的?然後試著多守住一些尚未來到的。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