焦點 | 時事分析
台灣GDP將超日趕韓⋯為什麼大眾卻無感?一文看懂GDP的起源與盲點

1.國內生產毛額GDP是由白俄羅斯的經濟學家西門.庫茲涅茨發明,可以揭露國家每年生產的一切商品和服務的金錢價值。
2.西門.庫茲涅茨認為GDP設計仍有瑕疵,計算過程不包含破壞環境的成本,及對人類生活有益的活動,因此警告不贏該把GDP當作衡量經濟進步的正常量度。
3.1944年參與布列敦森林會議的世界領袖決定戰後世界經濟選定GDP作為經濟進步的指標,美蘇冷戰時期雙方陣營更把GDP多寡當作國力強弱的象徵。
政府政策一向和促進資本擴張的利益有關,像是過去的圈地運動和殖民主義都是靠國家力量支持。但從1930年代初開始,在大蕭條(Great Depression)時期發生了某件事,使這些壓力變本加厲。
大蕭條嚴重破壞美國和西歐的經濟,各國政府手忙腳亂的尋找因應之道。在美國,官員找到西門.庫茲涅茨(Simon Kiznets),一位來自白俄羅斯的年輕經濟學家,請他設計一套會計制度,可以揭露美國每年生產的一切商品和服務有多少金錢價值。其概念是,如果你能更清楚看到經濟體在做什麼,就能推斷哪裡出了差錯且更有效的干預。庫茲涅茨設計了一個衡量標準,叫做國民生產毛額(Gross National Product,縮寫為GNP),GNP提供基礎給我們現在使用的量度:國內生產毛額(Gross Domestic Product,縮寫為GDP)。
GDP發明人反倒認為其計算過程有瑕疵
但庫茲涅茨很謹慎,他強調GDP有瑕疵。它總計貨幣化的經濟活動,但不在乎該活動是否有用或有害。如果你為了木材砍掉一座森林,GDP上升;如果你延長每日工時和延後退休年齡,GDP上升;如果污染造成就醫次數增加,GDP上升。但GDP不包括成本會計,它完全不提失去森林做為野生動物棲息地或碳匯的損失,也不提太多工作和污染對人民身心造成的傷害。
它不只遺漏壞事,也忽略很多好事,因為它不計算非貨幣化的經濟活動,即使那些活動對人類生活和福祉不可缺少。如果你種植自己的食物,打掃自己的房子或照顧年邁的父母,GDP一句不提。如果你付錢給公司替你做這些事,它才會計算。
庫茲涅茨警告,我們絕對不應該把GDP當作一個衡量經濟進步的正常量度。他認為我們應該改良它,將成長的社會成本納入計算,唯有如此,政府才會重視人類福祉及追求更均衡的目標。但接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。隨著納粹威脅升高,庫茲涅茨的福祉顧慮逐漸被淡忘。政府需要計算一切經濟活動,甚至負面活動,以辨認可以投入戰事的每一分錢和產能。最後這個更積極的GDP版本取得優勢。在1944年的布列敦森林會議(Bretton Woods Conference),當世界領袖坐下來決定治理戰後世界經濟的規則時,這個版本被奉為經濟進步的主要指標,恰恰和庫茲涅茨的警告背道而馳。
當然,衡量某些經濟活動而非其他事項,本來不是問題。不論衡量什麼,GDP本身對真實世界毫無影響。不過,GDP成長,就有影響了。我們開始關注GDP成長,就不只促進GDP衡量的活動,也促進那些活動的無限增加,不管付出的代價有多少。
GDP成長變成國力強弱的代表指標
起初經濟學家用GDP來衡量經濟產出的「水準」。水準是否太高,造成過度生產和供應過剩?或是否太低,導致人民無法獲得他們需要的商品?在大蕭條時期,產出水準顯然太低,為了走出衰退,西方政府重金投資基建計畫,並創造大量高薪工作,把錢放進人民的口袋,以刺激消費需求,使經濟再度活絡起來。這個辦法生效,GDP升上來了。但成長本身不是目標。別忘了,這是羅斯福總統主政的進步時代。史上第一次,目標是提高產出水準,為了改善人民生計和獲致進步社會成果的特定目的,和過去400年來的政府政策大相逕庭。換言之,早期進步政府把成長當作一個使用價值。
但好景不常。當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(OECD)於1960年成立時,它的章程列出首要目標是「推動政策來達到最高可持續的經濟成長率」,至今仍是一樣。突然間,目標不是追求更高產出水準以達到某個特定目的,而是最高成長率,無限期的為成長而成長。英國政府跟進,設定未來10年經濟成長50%的目標。這是極不尋常的擴張速度,也是成長第一次因其本身的緣故而被奉為國家政策目標。
這個概念如野火般蔓延。在冷戰時期,西方國家與蘇聯2大陣營之間的競爭變成主要用成長率來比拚。哪一個體制能最快增長GDP?當然,在這場競賽中,成長不只象徵強大,它也允許國家投資更多金錢用於軍事能力,並轉化為真正的地緣政治優勢。
這個為了成長而關注成長的新焦點,即成長主義(Growthism),永遠改變了西方政府管理經濟的方法。曾經用來改善大蕭條後社會成果的進步政策,諸如提高工資、組織工會和投資公共衛生和公共教育等施政方向,突然變成可疑。這些政策曾幫助人民福祉提高,但執行結果使勞工變得「太貴」,資方無法維持高利潤率。這段時期推出的環境法規也遭受質疑,因這些法規限制開發自然*。
*編按:美國環保署成立於1970年。
1970年代後期,西方經濟體的成長開始放緩,資本報酬率也開始下降。政府承受壓力,必須採取行動,替資方創造一個「解癮方法」。於是它們攻擊工會,修惡勞動法,以便降低薪資成本;它們刪除重要的環保法規,民營化過去禁止資方插足的公共資產,如礦場、鐵路、能源、水、醫療保健、電信等等,替私人投資者創造有利可圖的機會。1980零年代,美國總統雷根和英國首相柴契爾尤其狂熱的追求這個策略,開啟了我們稱作新自由主義的路線。
有些人傾向於認為新自由主義是一個錯誤,是過度極端的資本主義版本,我們應該拒絕它,迎回前幾十年盛行的比較人性化的版本。但當初轉移到新自由主義不是錯誤,它是受到成長義務的驅使。為了恢復企業利潤和挽救資本主義,政府必須將焦點從社會目標「使用價值」轉移到改善資本積累「交換價值」的條件。資本的利益被國家內化。到了今天,成長和資本積累之間的區別已幾乎完全消失。如今,目標是拆除利潤的障礙,把人類和自然變得更便宜,只為了成長。
西方國家將追逐GDP的成本轉嫁到南方國家
西方政府也把這個目標推到南方世界,同樣是為了解癮:替資方開拓新疆域。1950年代殖民主義結束後,許多新獨立的政府發展一條新的經濟路線。它們推出進步政策以重建國家,用關稅和補貼保護本土產業,改善勞動標準及提高工人薪資,投資公共醫療保健和教育。這一切都是為了扭轉被殖民主義的榨取,並改善人民福祉,而且確實有效。1960和1970年代,南方世界的平均所得以每年3.2%的速度成長。至關重要的是,在大多數例子中,成長本身不是目標,它是追求復原、獨立和人類發展的手段,和西方國家在從大蕭條後復甦的作為並無二致。
但西方強權不樂見這個轉變,因為這代表它們失去在殖民主義下享有的取得廉價勞力、原料和獨占市場的權利,於是出手干預。在1980年代債務危機期間,它們利用身為債權國的權力,運用它們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(IMF)的掌控,施加結構調整計畫於拉丁美洲、非洲和部分亞洲,除了中國和其他幾個東亞國家。結構調整強迫自由化南方經濟體,撤除保護性關稅和資本管控,降低工資和環保法規、削減社會支出、民營化公共財,一切皆是為了替外國資本撬開有利可圖的新疆域,及恢復廉價勞工和資源的使用權。
結構調整徹底重塑了南方經濟體。政府被迫放棄追求人類福祉和經濟獨立,改為聚焦於替資本積累創造最佳發展的環境條件。轉變以成長之名完成,但帶給南方世界災難性的後果。施加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20年的危機,導致貧窮、不平等和失業率節節升高。1980和1990年代,整個南方世界的所得成長率崩跌,跌到20年平均只增加0.7%的地步。但對資本來說,它有立竿見影之效,使跨國公司能夠公佈創紀錄的利潤,讓全球1%最有錢之人的所得暴增。西方世界的成長率恢復了,這才是結構調整的真正目的。但整個南方付出慘痛的人命代價,這個干預的遺緒是全球貧富差距在過去幾十年巨幅拉大。今日實質人均所得的南北差距,比1950年代殖民主義結束時多了4倍。
 書籍簡介
書籍簡介
《少即是多:棄成長如何拯救世界》
作者: 傑森.希克爾(Jason Hickel)
譯者: 朱道凱
出版社:三采
出版日期:2022/02/25
作者簡介
傑森.希克爾(Jason Hickel)
經濟人類學家、傅爾布萊特學者和英國皇家藝術學會會士。他出生於史瓦帝尼(舊名史瓦濟蘭),曾在南非與移工共事多年,撰寫種族隔離後的剝削問題和政治抗爭。出版過3本著作,最新一本是《鴻溝:全球不平等及其解決方案》(The Divide: A Brief Guide to Global Inequality and its Solutions)。他經常為《衛報》、半島電視和《外交政策》撰稿,並擔任歐洲綠色新政顧問及《柳葉刀》補償與重分配正義委員會委員。目前定居倫敦。
責任編輯:陳瑋鴻
核稿編輯:倪旻勤
商周大調查

2025大阪萬博全攻略》必逛展館、活動、門票、交通、美食景點推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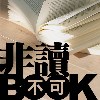
蒐羅與財經、職場、生活相關書籍內容介紹及書摘,協助讀者快速閱讀書籍精彩內容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